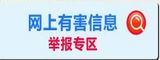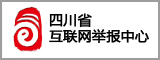四川“疫情”较为稳定,各个“场合”也逐渐开班了。笔者余事之一便是看戏。只因一桌二椅、靴网绫帕,总比真实人生要单纯得多。坐在堂厢或是楼厢,又或者就是一个“棚棚偏偏”搭出来的观众席位,一杯哪怕只是一次性纸杯泡的三花,心里不是暖和,便是清凉。

长久以来,很多民营剧团被称为“火把”。我却从不这样叫。总感觉,这就如同正儿八经的客家人被喊成是“土广东”那样有戏谑之意。我更愿意把这样的地方叫做“场合”。这样一来,总归是要正式一些。当今社会,民营剧团是极不易的。妆头、砌末,一手一脚都要靠自己。他们演出吸引的观众多是附近的老人。诚然,这些观众很热心。带着录像设备到现场,记录那些自己认为的美好。更有甚者,记录之后还要制作,制作之后还要发到网上。不得不说,这些老观众为戏剧事业的传播,默默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民营剧团的演员出名无路,这些观众的举动,无形中也成为了捧红演员的方式之一。到民营剧团看戏的老观众,会自觉地先去“佐”一些零钱,以备演员演到动情处往台口抛洒,表示自己对演员演技的叹服。四川这边还好,“抛”的情况几乎没有,一般都是放在台口,这样更显得观众对演员的尊重。
对民营剧团来讲,水牌子用油脂类的广告色已是一种奢侈。当然,因为擦洗较为不便的原因,用水粉类的亦是不简单的事。对于更多的民营剧团来讲,能用彩色粉笔就已经不错了。更何况,有的连彩色粉笔都没有。我们常常会在民营剧团的水牌子上看到一些“一简字”“二简字”,错字、别字等等。其实,不用去奇怪,更不用去责备。对民营剧团来讲,绝大部分演员没有机会读书,从小就接触班子。在发展并不景气和自身习惯成自然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巴幸不得每天都能粉墨登场。日久天长,换来的不是厌恶,而是酷爱和享受。虽然生活清苦,但乐在其中。这是在做真正的传承。而且,这样的传承既有根,又值得人尊敬。
连日落水,SN班就在这老天爷下个不停的雨中悄然开班了。我是第一次去,打车到公园、打伞到剧团,走了好长一截路。听到“一字板”的声响和旦角清脆的唱腔时,便寻声找到了这个隐藏在,一下雨门口的路面就形成泥泞小径的班子。刚到,一位热心的姐姐便从“报膀子”的角色中退出来,上前迎我。可能面对这样一副陌生面孔,再加上不是老大爷的年龄和打扮,她大概是不太相信我是来看戏的。
“来找人哇?”她微笑着问了一句。
我摇摇头说:“这儿可以看戏哇?”
她眼睛一亮说到:“可以!”
“扫哪儿喃?”
她一指墙上的微信二维码说:“扫这儿就可以了。”又赶紧一边往化妆间走,一边说到:“我马上给你泡茶。”
就在我刚刚扫完15块钱后,她就已经把茶泡好端到我面前了。我一亮码,她一点头,就招呼我随便坐在我想坐的位置。我就赶紧端起那杯用花哨一次性纸杯装的花茶,坐在离安全出口不远处的过道旁,开始欣赏台上的一举一动。

其实,坐下来时已经几乎是《归舟》的一半了。前面的《二美上路》已经错过。不过还好,之后的一两个小时还是比较饱和的。大概是刚刚开班,场面、衣箱、检场的人都不够,鼓师大概还管了小锣;《杀惜》大概是缺了笛子;《赔情》相雕的帽翅大概出现了在之前就有断裂或者未修复的前提下,又绑扎不稳的情况;班主帮忙捡场等等。尽管如此,每一位演员的认真程度还是令人感动。几乎每个折子戏演出期间,都有老观众在台口放钱。每放一次,台下掌声雷动。民营剧团观众的巴巴掌除了要拍给演员,还要拍给观众自己。这氛围,实在是在当今正规剧场感受不到的。
这天,台下的观众不多,约莫四十来往。但抢背、硬人都扎实,声腔、身段都到位。尤其是,当戏里宋江背身后,隐约现出那一身青褶子左肩上的补丁,就又应了那句“宁穿破,不穿错”的菊坛老话。这一点,恐怕是一些大剧团要走某些尝试性革新之路时,需要特别敬畏或者审慎为之的事。
就算我已经用口罩武装,还换了一身休闲的衣裳,也没能逃过班主的火眼晶晶。在台上的他,初见都一眼认出了是我。中场休息时,他递给我一杆“小熊猫”。因为素来没有喝烟的习惯,我拒绝了;快打幺台了,卸了妆的他跑到我的座位旁一拍肩膀说到:“走,去吃火锅。”因为还有事,更何况自己是一个普通观众,我也拒绝了;晚上,在一个戏剧群里,他用文字写到:“你嫂子认不到你,居然还买了票。”我也用文字写到:“肯定要买票,买票看戏,天经地义。”
二天到“场合”上,尤其是民营剧团看戏,我还是这个原则:全副武装,偷偷去看。

 四川法制网
四川法制网
 法治文化研究会
法治文化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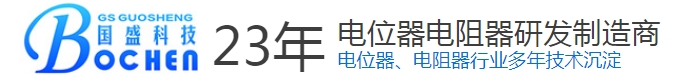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