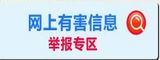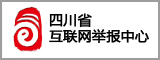“法官,产权证上明确了这是我的房子,王老二就该搬走!”
“这个房子是我们两家一起修的,老二住的就是我们自家的屋子,现在大嫂趁我在外打工偷偷去把产权办在自己名下,哪有这种道理?”面对大嫂和妻子的争执,说不出话的王老二只能在一旁干着急。而两妯娌之间的矛盾,还要从两家共同修建的房屋说起。
原告张大姐是王老二的大嫂,1997年王家兄弟在自家宅基地上共同修建了一栋二层同墙共壁的自建房,两家人在此居住多年,相处和谐。2007年,王老二因车祸导致头部受伤,丧失语言能力,落下残疾。其妻子长期在外务工并照料子女,对王老二的关心较少。因家庭矛盾,受伤后的王老二无奈之下搬到同墙的另一房屋内居住。几年后,王老大因病去世,妯娌间便因王老二所住房屋的归属产生矛盾。这次起诉,就是张大姐在房屋产权证办下来后,要求王老二搬出自己的家。了解到双方的基本情况后,我决定去王老二居住的地方看一看。眼前的场景和原告张大姐的描述相差无几,王老二的衣物等生活用品杂乱无章地堆放在案涉房屋内,该房间与他的家有一扇门可以自由通行,而自家的两间房已被妻子拆除,地上整齐的摆放着建筑材料准备重建。因为车祸后遗症,面对我的询问,王老二只能用手势和点头进行回应,在“交流”中我发现王老二对大嫂的起诉似乎并不反对,与其妻子的意见大相径庭。我更加疑惑了,既然不反对,那原被告双方的矛盾点在哪里?为什么居住多年后大嫂才起诉要求王老二搬走呢?带着疑问,我联系了双方所在地镇政府以及村社干部对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摸排了解。
村干部告诉我,王老二现在住的房子是张大姐家的,以前想着是两兄弟共同修建的,王老二住就住了,但是老二媳妇却对该房间的产权提出了异议,再让王老二继续住下去张大姐就不乐意了。加之,现在张大姐已经办理了房产证,明确了产权归属,所以才起诉要求王老二搬离涉案房屋。联想到王老二艰难的生活现状,我陷入了沉思。诉讼发生后,王老二妻子将自家的两间房拆除重建,搬回自己家已然不现实。而外出租房一方面需要额外的经济支出,且王老二车祸受伤残疾后从没有离开过现在的居所,与人交流也只是通过手势等肢体语言,临时换个居住地,对于残疾的他来说可能难以适应。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亲属关系,判决只会让双方在已有的矛盾裂痕再蒙上一层阴影,亲情也会陷入僵局,而双方还会继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势必衍生更多不必要的矛盾。而王老二作为残疾人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进退两难之际,我找到当地镇政府、司法所、村社干部共同协商解决办法,召集双方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协调,结合案件实际,我提议在不改变被告王老二现有生活习惯的前提下,促成两妯娌就王老二的居住问题达成共识。
面对处于矛盾焦点两端的大嫂和弟媳,我拟定了不同的调解思路。
对王老二的妻子我采取了教育+说服的方式。“现在房子的产权已经明确王老二所居住的房屋为大嫂家所有,从法理上说,王老二理应搬离;他在此居住了十余年时间,大嫂一家并未就此提出其他要求,保证了王老二的正常生活,从情理来说,也算仁至义尽。现在你丈夫身有残疾,作为妻子更应在生活上予以照顾,情感上多加支持,现在和大嫂对簿公堂纠缠于诉讼,实际上也会对丈夫的心理造成伤害。”另一边,面对原告张大姐,我则更多地予以了肯定。“家人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是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传统美德,正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大哥虽然不在了,但他和兄弟之间的血缘并没有因此消散,相信你作为大嫂也不愿意看到自家兄弟流离失所……”面对我的劝说,想到老二这些年的境遇,张大姐忍不住湿了眼眶。我趁热打铁,提出“现在他们家要重建房子,这个期间能否让老二继续住在现在的房间里?”
就这样,我一边进行亲情的修复,一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的沟通,双方在镇村干部的见证下达成协议:在家中修建房屋期间,王老二继续居住在案涉房屋内,待自家房屋修建好后,再搬回新房内居住,张大姐自愿申请撤回起诉。
案子顺利解决了,王老二的住处有了着落。我想,这份写在助残日前的“答卷”,我可以交卷了。

 四川法制网
四川法制网
 法治文化研究会
法治文化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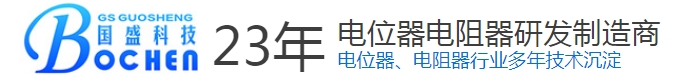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